談談余秀華的詩歌現象
靈魂超度者的詩意寫作
——從余秀華的詩歌現象說起
黃葉斌
(一)
自從“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”的一首現代詩在中國詩壇熱鬧以來,讀者對于余秀華的詩歌及其個人的褒貶,眾說紛紜莫衷一是。筆者以為,這是一種值得慶幸而關注的詩壇現象,也是一種對于弱勢群體詩人的別樣呵護與鼓勵。
盛名的賜予與特別的關注,對于余秀華來說,是一把雙刃劍。她先后被評論家認為是“中國的艾米莉·狄金森”,“應該是中國排在前十的女詩人”,六次獲得國家級和省級文藝創作獎項,應邀走進中央電視臺“朗讀者”節目錄像,還在英國本色表演個人詩歌的情景劇。另外,她已經出版發行了十余本詩歌散文小說集,并獲得不菲的版權專利,優酷為她拍攝紀錄片,成名詩被歌手譜曲爆紅網絡。這些業績,是她的個人文學創作的成就使然,也是新世紀以來,我國的互聯網發展和社會改革開放的紅利使然。同時,網上對于她的詩歌藝術成就的激烈爭論或對立臧否,也是活躍了文壇的氣氛,激活了不同創作觀念與藝術標準的討論。所以,這是她的文學創作的華麗轉身與精彩亮相,是為家鄉人才輩出時代的代言人,是弘揚傳承民族傳統文化的鄉村踐行者,更是新時代殘疾女性自尊和才華的典型代表與集中展示。至于因為出名或性格等問題而使得她離婚兩次,這個可能是她的負面效應吧。不管怎樣,對于她個人來說,還是一種利大于弊的人生閱歷吧。
(二)
閱讀余秀華的詩歌,我們似乎感覺到一種別樣的心靈呼喚和靈魂戰栗。她的詩歌,在敘述內容的主題上,幾乎與個人的身體、家事、農具、莊稼、動物、農民和愛情相關聯,也與殘缺身體的體驗、經歷疼痛的記憶和意象想象的幻覺糾纏。搖晃的人生與腦癱的搖晃,特殊的身份與社會角色,使得她在觀察、探尋自身和萬物的過程中,有著與他人不一樣的視角與敏感,不一樣的聯想與想象,不一樣的提煉與升華。
她是詩中的女性抒情者,注重身體性的寫作。她常常以“傻子、犯病者、癡情者、孤獨者、奉獻者、自戀者和逃離者”自居(如《與一面鏡子遇見了》、《面對面》、《在田野上打柴火》、《戰栗》、《人到中年》、《我養的狗,叫小巫》、《我的身體是一座礦場》、《我愛你》、《茍活》等),對于愛情、友情和親情的渴望與再現,似乎以一種自虐、自慰、自嗨的形式實現,用語大膽而粗狂,情懷熾烈而深沉,呼告簡潔而直白。愛欲的躁動與呼喚、愛欲的幻滅與撫慰,這些復雜而靈動的意蘊,表面上看,是一種情欲的覺醒和感受的表露,實際上是作者借助于詩歌,對于生命與尊嚴、生活與質量、人生與意義、存在與死亡的形而上哲學主題的追問與選擇。這些個性鮮明的詩意主體形象,不僅是她個人的神態載體,更是代表著一類殘疾者的心聲與呼吁。
同時,她也是詩外的理性觀察者與道德評判者。如何從自卑、自閉的生態環境中走出來,作者以一個生命拯救者和悲苦終結者的姿態,進行了有形而有效的嘗試和自審而自覺的救贖。她寫作詩歌,意識到就是一種身體和靈魂的突圍與構建,就是感官和精神與世界的對接與融洽。她渴望外界的人類和萬物認識自己、接納自己、理解自己、提升自己,從而獲得一種不被人遺忘或誤解為異己的超度。在其詩集《且在人間》、《無端歡喜》、《我們愛過又忘記》、《搖搖晃晃的人間》、《月光照在左手上》中,作者以真誠的心語和直率的告白,褪去扭捏造作的姿態和欲言又止的含蓄,直面人生的常態、困頓的丑態與尷尬的窘態,以自嘲和自洽的方式,為自己,也是為他人尋求獨處的美感與寂寞的快意,同時也為個人在身體的殘缺處,找到補救傷痕與填補空虛的靈丹妙藥。這種與靈魂的對話,使得她的詩歌的共情賦能,有著無人能比的感染力和感召力。當然,有些詩歌的理解,由于其意象的跳躍性、思維的非邏輯性和語言的不規則性,使得部分讀者在生命體驗的差異中對其產生一種霧里看花的印象,也是情理之中無可厚非的。
(三)
余秀華詩歌的表達形式與語言特點,是眾多讀者對其或津津樂道或非議抨擊的分歧所在。
現代詩歌的特點,以白話文為載體,以古典詩詞的美學傳統為根基,以意象的選擇和描述為表象,以語言分行排列的形式為模式,以情感的意蘊為目的,使得讀者能夠與作者一起獲得理解與共鳴。自上世紀新文化運動以來,我國現代詩的寫作與普及,已經達到了一種較高的水準,如冰心、徐志摩、戴望舒、余光中、卞之琳、何其芳、艾青、鄭愁予、舒婷、席慕蓉、海子、食指、臧克家、汪國真等詩人,他們的創作成就及其影響,為今天的寫作者提供了藍本和經驗。而余秀華的詩歌,在其藝術成就方面來說,似乎讀者評述的并不多,而是重點在于她的情感的噴發與意象的組合,給予讀者突兀、大膽、凜冽和直率的感覺。但是,她的現代詩的模仿痕跡與創新能力,與其主題內容的對接還是基本吻合的,其詩歌的感染力和張力,往往能夠使讀者產生一種驚奇、驚訝和艷羨的贊嘆。比如,“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”,就是道出了人人心中有而個個筆下無的人間情懷。
語言的流程與意象的搭配,是詩歌意境的重要體現。如《一打谷場的麥子》中,“五月看準了的地方/從天空垂直打下/做了許久的夢墜下云端/落在金黃里/父親又翻了一遍麥子/—內心的潮濕必須對準陽光/……”詩句中,作者將“天空、夢、金黃、陽光、潮濕”等意象集合在一個特定的時空里,把父親的勞作與個人的感受,通過嫁接的思緒與場景的勾連,作者想著“如果在這一打谷場的麥子里游一次泳/一定會洗掉身上的細枝末節/和抒情里所有的形容詞/怕只怕我并不堅硬的骨頭/承受不起這樣的金黃色”。這里的“游泳、形容詞、骨頭、金黃色”等詞語的運用,具有通感的妙用和靈感的機靈,虛實結合的組合,曬谷場與陽光的質感,與“游泳”的特點連接起來了,同時,也暗含著作者暗淡的傷感與惆悵。
把詩歌的情趣和慰藉化為一種治療淡化身體疼痛感的良藥秘方,可能是作者的一種生存哲學和生活甜點吧。我們發現,在她的大部分詩歌中,作者的不甘心、不屈服、不認命的倔強與頑皮,似乎總是在一種調侃、詼諧、幽默的語境中展開。可見,詩歌的伊甸園,就是作者的心靈野馬自由馳騁的自留地,就是她的靈魂俯瞰世界的制高點,就是她的無冕之王的制作工廠,就是她的獨具特色的審美視域。
俗話說,“憤怒出詩人”,套用這句話,也可以是“殘疾出詩人”,比如北京史鐵生的病隙雜記、河北提暢的500首詩詞,陜西胡少杰的近體詩,還有國外的古希臘盲詩人荷馬、英國盲詩人彌爾頓、美國盲聾啞詩人海倫·凱勒、埃及盲人作家艾哈·侯賽因、愛爾蘭腦癱作家克里斯蒂·布朗、俄國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等,他們的身世與成就,曾經激勵鼓舞了無數殘疾人的斗志與生活的勇氣,并在面對絕望和困難時,始終堅持自己的夢想和目標,從而走向人生的輝煌。
對抗人世間的厄運或殘疾的身軀,是坦然面對,是委曲求全,是自甘墮落,還是奮力一搏?實踐證明,其最好的辦法,就是把一切不如意之事化為時光之壁的回音,把內心的悲哀和憋屈化為詩詞韻律的顫音,把他人的嘲諷和蔑視化為向上向善的福音。正如作者所言:“詩歌是靈魂的自然流露”。如此,讀者從余秀華的詩歌中,也就獲得了一種無窮的啟示與深刻的回味。
(寫于2025.02.26 約2770字)
——從余秀華的詩歌現象說起
黃葉斌
(一)
自從“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”的一首現代詩在中國詩壇熱鬧以來,讀者對于余秀華的詩歌及其個人的褒貶,眾說紛紜莫衷一是。筆者以為,這是一種值得慶幸而關注的詩壇現象,也是一種對于弱勢群體詩人的別樣呵護與鼓勵。
盛名的賜予與特別的關注,對于余秀華來說,是一把雙刃劍。她先后被評論家認為是“中國的艾米莉·狄金森”,“應該是中國排在前十的女詩人”,六次獲得國家級和省級文藝創作獎項,應邀走進中央電視臺“朗讀者”節目錄像,還在英國本色表演個人詩歌的情景劇。另外,她已經出版發行了十余本詩歌散文小說集,并獲得不菲的版權專利,優酷為她拍攝紀錄片,成名詩被歌手譜曲爆紅網絡。這些業績,是她的個人文學創作的成就使然,也是新世紀以來,我國的互聯網發展和社會改革開放的紅利使然。同時,網上對于她的詩歌藝術成就的激烈爭論或對立臧否,也是活躍了文壇的氣氛,激活了不同創作觀念與藝術標準的討論。所以,這是她的文學創作的華麗轉身與精彩亮相,是為家鄉人才輩出時代的代言人,是弘揚傳承民族傳統文化的鄉村踐行者,更是新時代殘疾女性自尊和才華的典型代表與集中展示。至于因為出名或性格等問題而使得她離婚兩次,這個可能是她的負面效應吧。不管怎樣,對于她個人來說,還是一種利大于弊的人生閱歷吧。
(二)
閱讀余秀華的詩歌,我們似乎感覺到一種別樣的心靈呼喚和靈魂戰栗。她的詩歌,在敘述內容的主題上,幾乎與個人的身體、家事、農具、莊稼、動物、農民和愛情相關聯,也與殘缺身體的體驗、經歷疼痛的記憶和意象想象的幻覺糾纏。搖晃的人生與腦癱的搖晃,特殊的身份與社會角色,使得她在觀察、探尋自身和萬物的過程中,有著與他人不一樣的視角與敏感,不一樣的聯想與想象,不一樣的提煉與升華。
她是詩中的女性抒情者,注重身體性的寫作。她常常以“傻子、犯病者、癡情者、孤獨者、奉獻者、自戀者和逃離者”自居(如《與一面鏡子遇見了》、《面對面》、《在田野上打柴火》、《戰栗》、《人到中年》、《我養的狗,叫小巫》、《我的身體是一座礦場》、《我愛你》、《茍活》等),對于愛情、友情和親情的渴望與再現,似乎以一種自虐、自慰、自嗨的形式實現,用語大膽而粗狂,情懷熾烈而深沉,呼告簡潔而直白。愛欲的躁動與呼喚、愛欲的幻滅與撫慰,這些復雜而靈動的意蘊,表面上看,是一種情欲的覺醒和感受的表露,實際上是作者借助于詩歌,對于生命與尊嚴、生活與質量、人生與意義、存在與死亡的形而上哲學主題的追問與選擇。這些個性鮮明的詩意主體形象,不僅是她個人的神態載體,更是代表著一類殘疾者的心聲與呼吁。
同時,她也是詩外的理性觀察者與道德評判者。如何從自卑、自閉的生態環境中走出來,作者以一個生命拯救者和悲苦終結者的姿態,進行了有形而有效的嘗試和自審而自覺的救贖。她寫作詩歌,意識到就是一種身體和靈魂的突圍與構建,就是感官和精神與世界的對接與融洽。她渴望外界的人類和萬物認識自己、接納自己、理解自己、提升自己,從而獲得一種不被人遺忘或誤解為異己的超度。在其詩集《且在人間》、《無端歡喜》、《我們愛過又忘記》、《搖搖晃晃的人間》、《月光照在左手上》中,作者以真誠的心語和直率的告白,褪去扭捏造作的姿態和欲言又止的含蓄,直面人生的常態、困頓的丑態與尷尬的窘態,以自嘲和自洽的方式,為自己,也是為他人尋求獨處的美感與寂寞的快意,同時也為個人在身體的殘缺處,找到補救傷痕與填補空虛的靈丹妙藥。這種與靈魂的對話,使得她的詩歌的共情賦能,有著無人能比的感染力和感召力。當然,有些詩歌的理解,由于其意象的跳躍性、思維的非邏輯性和語言的不規則性,使得部分讀者在生命體驗的差異中對其產生一種霧里看花的印象,也是情理之中無可厚非的。
(三)
余秀華詩歌的表達形式與語言特點,是眾多讀者對其或津津樂道或非議抨擊的分歧所在。
現代詩歌的特點,以白話文為載體,以古典詩詞的美學傳統為根基,以意象的選擇和描述為表象,以語言分行排列的形式為模式,以情感的意蘊為目的,使得讀者能夠與作者一起獲得理解與共鳴。自上世紀新文化運動以來,我國現代詩的寫作與普及,已經達到了一種較高的水準,如冰心、徐志摩、戴望舒、余光中、卞之琳、何其芳、艾青、鄭愁予、舒婷、席慕蓉、海子、食指、臧克家、汪國真等詩人,他們的創作成就及其影響,為今天的寫作者提供了藍本和經驗。而余秀華的詩歌,在其藝術成就方面來說,似乎讀者評述的并不多,而是重點在于她的情感的噴發與意象的組合,給予讀者突兀、大膽、凜冽和直率的感覺。但是,她的現代詩的模仿痕跡與創新能力,與其主題內容的對接還是基本吻合的,其詩歌的感染力和張力,往往能夠使讀者產生一種驚奇、驚訝和艷羨的贊嘆。比如,“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”,就是道出了人人心中有而個個筆下無的人間情懷。
語言的流程與意象的搭配,是詩歌意境的重要體現。如《一打谷場的麥子》中,“五月看準了的地方/從天空垂直打下/做了許久的夢墜下云端/落在金黃里/父親又翻了一遍麥子/—內心的潮濕必須對準陽光/……”詩句中,作者將“天空、夢、金黃、陽光、潮濕”等意象集合在一個特定的時空里,把父親的勞作與個人的感受,通過嫁接的思緒與場景的勾連,作者想著“如果在這一打谷場的麥子里游一次泳/一定會洗掉身上的細枝末節/和抒情里所有的形容詞/怕只怕我并不堅硬的骨頭/承受不起這樣的金黃色”。這里的“游泳、形容詞、骨頭、金黃色”等詞語的運用,具有通感的妙用和靈感的機靈,虛實結合的組合,曬谷場與陽光的質感,與“游泳”的特點連接起來了,同時,也暗含著作者暗淡的傷感與惆悵。
把詩歌的情趣和慰藉化為一種治療淡化身體疼痛感的良藥秘方,可能是作者的一種生存哲學和生活甜點吧。我們發現,在她的大部分詩歌中,作者的不甘心、不屈服、不認命的倔強與頑皮,似乎總是在一種調侃、詼諧、幽默的語境中展開。可見,詩歌的伊甸園,就是作者的心靈野馬自由馳騁的自留地,就是她的靈魂俯瞰世界的制高點,就是她的無冕之王的制作工廠,就是她的獨具特色的審美視域。
俗話說,“憤怒出詩人”,套用這句話,也可以是“殘疾出詩人”,比如北京史鐵生的病隙雜記、河北提暢的500首詩詞,陜西胡少杰的近體詩,還有國外的古希臘盲詩人荷馬、英國盲詩人彌爾頓、美國盲聾啞詩人海倫·凱勒、埃及盲人作家艾哈·侯賽因、愛爾蘭腦癱作家克里斯蒂·布朗、俄國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等,他們的身世與成就,曾經激勵鼓舞了無數殘疾人的斗志與生活的勇氣,并在面對絕望和困難時,始終堅持自己的夢想和目標,從而走向人生的輝煌。
對抗人世間的厄運或殘疾的身軀,是坦然面對,是委曲求全,是自甘墮落,還是奮力一搏?實踐證明,其最好的辦法,就是把一切不如意之事化為時光之壁的回音,把內心的悲哀和憋屈化為詩詞韻律的顫音,把他人的嘲諷和蔑視化為向上向善的福音。正如作者所言:“詩歌是靈魂的自然流露”。如此,讀者從余秀華的詩歌中,也就獲得了一種無窮的啟示與深刻的回味。
(寫于2025.02.26 約2770字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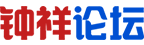

望天
粉絲 80 關注
江漢豚
粉絲 4556 關注
東坪村民
粉絲 1276 關注
鄉民
粉絲 105 關注
鄭重其事
粉絲 20 關注
贊過的人